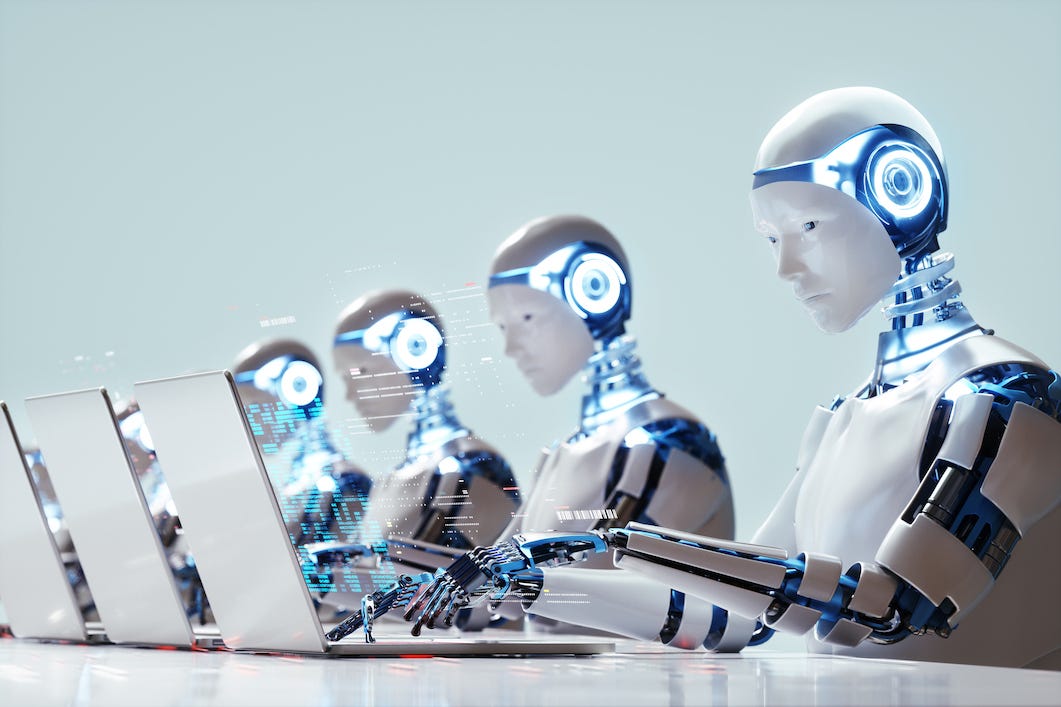九年前,我设法进入了通常密封世界的空间:斯坦福人人工智能实验室。我想了解这种应该改变一切的现象。我报道了A.I.之间的一次会议研究人员和风险资本家正在寻找下一件大事。碰巧的是,他们讨论的话题是如何使用AI。我引用了“取代所有作家。”我在那里,墙上的作家。
这是一些重大的破坏,此后不久,我在下面的调度中写了一篇文章,一群非作者辩论如何替换所有作家。我正在仔细记录笔记,以便未来的替代作家将有一些记录,记录了清洗的情况。
好吧,在这里。
当时,调度尚未发布,因为它不适合我的书进行。我最近重新审视了它,并被回想起来的我们现在在那里孵出的方式感到震惊。
因此,我现在就发布了它,这是对未来预测的过去的一瞥。这是一段漫长的读物,因此在有时间的时候就潜入或保存一会儿。我希望你喜欢它。
由Anand Giridharadas
A.I.的故乡斯坦福大学的大楼大楼实验室。
在湾区外,我在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度过了几天。该实验室占据了盖茨计算机科学大楼的两层楼。这是一个暗淡的办公室和会议室。如果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有人将您蒙住眼睛并将您存入其中,而您以某种方式未能注意到所有机器人和方程式,那么您可能会猜想您是一家中学体育奖杯的中型制造商的区域销售部门。
气氛中没有任何建议。没有什么告诉您这是催生Google的地方。然而,非常聪明的人说,他们在这里炮制的未来可能会改变人类文明的面貌。有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将使天堂陷入地球。其他人担心这是我们最接近地狱的人。
天堂的场景使人类的存在变得毫不费力,无缝,健康,不朽,高效,悠闲,聚宝盆,创造力。人工智能。已经猜到了您在寻找事情时正在寻找的东西,将来它会在生活的每个领域都知道您的所有需求。人工智能。已经决定何时告诉新父母,新生儿可能不会呼吸,并且在未来的疾病康复中,纳米机器人和大数据压缩的超级计算机可能会终止衰老,甚至垂死。人工智能。已经在美国交易所交易了所有股票的一半,将来它可能会使我们所有人摆脱工作负担,并让我们绘画和写十四行诗和舞蹈。通过给予人类对健康和环境的掌握,AI。可以说,可以使我们成为第一个避免灭绝本身的物种。
然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电动汽车和火箭船的建造者,所有技术称为A.I.世界上最大的存在威胁,并宣称,通过人工智能,我们召集了恶魔。这是地狱的情况。它不太精确,不确定,因为它专注于人类在建立替代工具时可能无法预见的东西。LinkedIn的Reid Hoffman比较A.I.开发可能会对地球产生重大影响的未知物种。人道主义者也担心,人工聪明的未来本质上是未来的,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除了A.I.及其算法。教皇弗朗西斯(Pope Francis)警告说,机器人技术和相关的进步可能会独自一人,导致人类的破坏是由一个无情的机器代替的,或者将我们的星球转变为一个空旷的花园享受少数人的享受。最可怕的愿景本身或在坏人手中,加快了我们的灭绝日期。
处理此类事情是很大的压力。这就是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的命运实验室的实验室,今天晚上驶入二楼休息室。有时,这就是文明的重塑方式:经常通过高度社会上的尴尬的人被认为是由一个像机器人一样的人类来重塑的人,他们选择使机器人更像人性化。
从实验室花费的几天开始,我与我在一起的最多是这次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因为在那次会议中,我能够看到,就像我以前那样清楚的那样,硅谷的预测言论是如何有效的:如何使用一种奇怪的未来主义和愤世嫉俗的鸡尾酒来证明一个将是合理的世界。对大量人造成毁灭性,对其预测因素非常出色。以及培养和相信自己无能为力的想法如何成为夺取权力的重要工具。
***
今晚是实验室eClub的每两周一次会议,该会议将自己描述为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SAIL)与一群公司合作伙伴之间的第一个正式联盟,以促进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与感兴趣的风险投资者之间的讨论在现实世界中,AI应用程序。技术人员必须认识硅谷的金钱人,他们在Sand Hill Road上工作了几个街区和一个世界。也是思想领导者的金钱男人瞥见了尖端的技术,这些技术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下一个独角兽。
今天的会议的话题是新闻和写作。他们试图弄清楚是否以及如何取代所有作家,就像其中一位所说的那样。
与风险资本家建立联盟的津贴:侧面的一张桌子上覆盖着Pronto的披萨,一瓶黑比诺和一些啤酒。披萨以每分钟几片的速度消失。黑比诺将保持未打开,但有些啤酒正在饮。
大约二十名学生开始坐下。许多牛仔裤,许多手腕活动跟踪器,膝盖上的许多腰双腿,许多天才,许多热心和不耐烦的男性能量因社交意识或社会恩典而无光彩。房间里有一个女人。在接下来的九十分钟内,她不会说话。
在房间的一个角落,一对风险投资家。有一个男人,我会叫马蒂(Marty对所有事物的无聊,认为他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最好的想法,并且有很多钱。在他旁边是一个男人,我将称为海湾另一家顶级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阿什什(Ashish),他为这个房间的人们提供了更现实的理想。他是印度人,很帅,不富有富裕,但富有,都穿着完美合身的深色衣服,既运动又正式,播放了我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伴侣。他曾经是。当您在Google中搜索他的名字时,建议(A.I。)提出的第一个其他查询是“灰烬______净资产”。也!他驾驶微型飞机!他要从斯坦福医学院离开!马蒂(Marty)和阿什什(Ashish)共同代表了数十亿美元的渴望,以投资于像这些技术人员这样的孩子。
我坐在一个名叫Manoush的学生旁边。他很自如,认真,有些敌对。我问什么把他吸引到了AI。他说要让人们摆脱工作的繁琐。让机器,算法做重复的事情。自由人们思考大型战略思想。
他说,导致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因素是劳动力的效率。”
不打算,我一定看起来持怀疑态度。Manoush告诉我自己查找引文。
A.I. Manoush的愿景有些紧张。界。少数A.I.的开国元勋,其中一些人出席了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这是该领域的宪法公约,对他们的原始项目感叹,他们使用计算机来寻求理解和模仿人类 -已经取代了提高生产力的更平淡和利润的目标。像帕特·兰利(Pat Langley)这样的易怒的老年人可以哀悼人工智能中的情报被定义为执行复杂,多步推理的能力,了解的含义自然语言,设计创新的人工制品,生成实现目标的计划,甚至是关于自己推理的理由。现在,事情必须在市场上证明自己是合理的。兰利写道,尼基·阿西(Niche A.I.人工智能。实验室放弃了该领域的最初目标。最近的研究并没有创建与人类具有相同广度和灵活性的智能系统,而是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但狭窄的白痴。
Manoush深深地相信白痴熟练的人。这些机器人可以释放大量的人类能量。但是,我问Manoush,所有临时甚至永久地都会被搁浅的人呢?
Manoush说,我们有要脱身的人。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将为整体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
如今,这是海湾周围的一篇重要信仰。这些男人和女人知道他们的发明可能会令人恐惧。他们的承诺是,这是在平静之前的风暴,在解放前的席位。
当然,即使是在实验室内,也有一些人质疑这一愿景。哥伦比亚研究员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 Niebles)嘲笑机器人的流行文化图像杀死并吃了人类的大师。但是他担心对他来说其他威胁似乎是现实的。他想知道:A.I.由他的实验室培养的特工会造成大规模失业?当复杂的机器从事许多旧工作时,人们是否需要获得最低收入?我们将如何占据人们的时间,精力和想象力?niebles不必担心启示录。他担心自己比这个时代的许多赢家更加自我意识,因为他正在创建一个新世界,这将为像他这样的人而有所回报和充实。
但是他赶紧补充说,他没有时间考虑此类问题。我们想到:实现新事物的障碍是什么?”他说。技术问题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们挤满了反思。AI。他说,研究人员的自我态度是站在我们和进步之间的障碍的封锁者。想到后果并不是他们习惯。
***
目前,一个名叫罗伯托(Roberto)的意大利博士后打电话给会议,并介绍了一些问题以构建对话。A.I.怎么能帮助每个人的利益个性化新闻?它如何挖掘数据和模式中隐藏的故事?它可以复制特定作家的风格并在声音中产生新鲜的内容吗?
应该指出的是,没有记者参加这次对话。(我是一个沉默的观察者。)在缺席的情况下重新想象人们的生活并不那么尴尬。
一些聚会始于需要解决方案的问题。其他人则从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开始。这是后一种类型的会议。新闻业当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房间里似乎没有人对这些问题有很多了解。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些问题就会激励他们的动力。他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他们正在发明他们认为不可避免的传播技术,他们想看看这些技术可以为 - 或对新闻业做些什么。
房间里的一个重要的自信似乎是这样:它们是曲线的外推者,是部队的先知。说他们想要什么世界不是他们的角色。他们的工作是通过说这会发生的东西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
Manoush使事情变得有所了解,以了解将来谁应该引起新闻。曲线正在向大型互联网门户推动越来越多的世界互联网流量和广告资金。根据纽约时报,在莫诺什讲话的季度中,只有两家公司(Facebook和Google)捕获了在网上广告上的新资金中的85%。(这两家公司恰好是实验室的主要招聘人员。)
对我来说,似乎很明显的是,新闻应该朝着分发迈向能够做广告的人要比《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更好的人,因为他们只是对您没有足够的数据。
这是技术圈子中的一个理想的想法:技术应该吃媒体,就像它应该吃的其他所有东西一样。在Manoush所设想的将来,地球上最强大的实体也将作为对自己能力的检查。但是他没有出于对世界的任何信仰而提出的想法。对他来说,似乎很明显,新闻应该朝着广告收入的曲线趋向于任何地方。
一个温柔但抗议的良好 - 从Manoush射出了几个座位。是埃莱克(Elek),看起来像比约恩·博格(Bjorn Borg)和耶稣的混合物。我将在某种程度上竞争,”他微微地说。
顺便说一句,这样您就不会感到震惊,这并不令人不快,因为实验室中的分歧往往没有E.Q。商业世界的善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而我唯一的推动地点是;•仅基于这一点,并将其朝着稍微不同的方向带走;我认为这主要是真的,但是当您不同意正在进行的评论时,您向前倾斜,脖子僵硬,有时甚至是下巴有些振动,也许称为露出一个没有掩盖您蔑视的笑容,然后您发射了。
有些人和直接的人一起去了 - 不,不,不,不,否否
其他人则喜欢更温柔但仍然直接的 - 我的意思是,但是
或者,有一次,我不喜欢这个想法的原因 -
好吧……埃莱克说。我将在某种程度上竞争。
Manoush转向Elek,两个脖子现在都很僵硬,都有假的笑容:
埃莱克说。•新闻中有很多钱,而《纽约时报》是贪婪的,然后,是的,Facebook应该在其中占用更大的份额。或者新闻中没有很多钱,《纽约时报》正在争先恐后。而且,如果Facebook占用了更大的份额,那么将会发生的事情不是世界变得更好,而是所有作家都被解雇了。然后没有任何人的消息。
Elek,您会注意到,与Manoush的合理性不同。Manoush看到了一条曲线,并预言了它所暗示的未来。Elek看到了曲线,但并不认为我们注定要遵循它。他以为我们有选择。事实证明,他在房间里的这种观点中并不独自一人,尽管他只有很小的少数。少数民族完全由欧洲人组成。他们有一些历史,当人们谈到一个没有作家的社会时,也许听到了警钟。
然而,埃莱克和他的欧洲同胞一边代表,思想领导者及其门徒倾向于吸引Manoush的观点。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最美好的时代,在一个无休止的自我完善世界中,谁需要那种怀旧的埃莱克(Elek)的批判性新闻?
``我期待新闻界涵盖所有辛勤工作和辛劳的时代,而不是遭受颠簸的公司的厄运,忧郁或羞耻感。伙伴叫乔什·埃尔曼(Josh Elman)发推文。当亲爱的创业公司Theranos是《华尔街日报》调查的主题时,质疑其对血液测试业务的基本真实性时,年轻的创始人被激怒了:巫婆狩猎对@Theranos的hind狂。是的,需要更多的透明度,但是创新将有错误的位置。但是,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烧毁努力?山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格雷厄姆回答:我认为您感到惊讶的是,不是成为失败者自己,而是您低估了嫉妒的力量。许多思想领导者几乎不会介意Google和Facebook'他们喜欢称呼它的消息。
***
然而,今晚埃莱克有一个不太可能的盟友。坐在角落里的马蒂(Marty)对所有Facebook的演讲感到恼火。他开车去听一些技术人员告诉他,新闻的未来在于像他这样的家伙已经建立了。
马蒂说,如果我们回到这些会议的背景下,却享受了良好的权威,我们试图思考您可以创建有趣的新业务的方法。”提供了一些点燃:如果Uber想用机器人代替所有驱动程序,我们是否想用AID代替所有作家?我会在那里停下来。令我惊讶的是,这些是我们应该在这里谈论的事情。
现在我们在说话。这是一些重大的破坏:一群非作业者辩论如何替换所有作家。我正在仔细记录笔记,以便未来的替代作家将有一些记录,记录了清洗方式的下降。
另一个V.C. Ashish给Marty提供了一些帮助,暗示他们讨论了一种算法来创建内容。可能会吸引最多的眼球。该网站正在放置AI。已经工作了,尽管目前仍然涉及人类。
Ashish说:``Ashish说:“许多列表通常都是使用此工具完全策划或建议的,他们拥有的内部工具可以在Twitter,Facebook等上共享各种链接。” Ashish说。该工具将网络扫描以获取病毒爆发。也许它在有关纸杯蛋糕的帖子中发现了一个上升。它分析了它们的模式。'基本分类技术(例如弦匹配)可以告诉您,这几个链接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这与纸杯蛋糕的外观都需要相似。标题上有一个,并选择了十四个最好的例子,现在已经开始趋向于BuzzFeed的趋势释放了趋势。
艾希什说,事实证明人们真的很喜欢这种内容。因此,也许这意味着我们要盯着您拥有AI的未来。帮助创建内容;它看起来更像是Buzzfeed,而不是纽约的专家。”笑声充满了房间。这也许我们实际上都想阅读的内容。
阿什什(Ashish)刚刚展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领导者的举动:声称给人们想要的东西的人造宗教主义,这恰好对像您这样的人带来了回报。
整个房间的欧洲脖子僵硬。是罗伯托。
但是那能走多远呢?”他说。因为归根结底,有人需要去那里拍照。而且有人需要坐下来写下原始的东西,即您会变形。但是原始内容是由某人支付的。
再次,在这里,欧洲人之一正在参加辩论,并提供了一些睁大眼睛的理想主义。它在这个房间里是理想主义的,因为它提高了需要选择的视野,这与曲线可能带来的视野不同。
阿什什(Ashish)通过提醒曲线的力量来迅速将罗伯托(Roberto)放在他的位置:我认为,只要互联网免费,就会有足够的用户生成的内容,这将使人们能够允许人们编译那里最有趣的事情。这是一个普通的山谷避免:将来,这个消息将是普通人发布的照片,视频和文字的最佳收藏。
但是,如果作家想拯救自己,阿什什说,有办法。例如,他们可以加入Patreon,该平台允许艺术家众包顾客寻找自己的小型美食家。换句话说,将来企业家正在建立,生存的方式是成为一名企业家。毕竟,企业家精神的兴起是山谷正在赌博的另一条曲线。
现在,另一个欧元的家伙,有两色调的棕色和金色的头发以及更多的欧洲人性主义,僵硬了脖子并想要进来。他没有购买这个赞助的想法,假设人们会为高质量的写作付费。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人关心好的专辑,而他们只关心谈论感情,那么没有人会为此付出代价。”再次,欧元在曲线趋向于趋势和好处之间有所区别。
Ashish将一无所有。新闻的价值是什么?”他问,笑着说。
两色调的欧元仍然令人沮丧:一旦您告诉人们要支付五美元,否则您可能会得到一个非常卑鄙的版本,而BuzzFeed制作的标题也可能不再支付五美元……
Ashish不想成为一个沮丧。除了赞助外,他在新闻业中还有另一个亮点。一个名为“信息”的网站最近席卷了硅谷,其订阅价格便宜。根据Ashish的说法,这就是为什么信息很好。因为它有助于人们赚钱,而不是对民主和公民身份提出一些模糊的欧元理想。
他说,他们的订户基础是他们经常写的人。”他说。在沙丘路上,很多人。许多在科技公司执行职位的人。他们愿意为这些内容付费,因为它们几乎是必要的。业务信息。您不阅读,有点新闻。现在对您的业务至关重要。
***
随着对话的进行,新闻业的未来正在揭示自己:无薪用户生成的有关纸杯蛋糕的内容,由bots自动选择,以策划为列表列表;记者 - 企业家抚养自己的赞助;关于社会 - 麦加嗪模型的高级内容,涵盖了伟大和善良的新闻和对他们的伟大和善于消费。
但是现在在这里,罗伯托(Roberto)以他的欧洲节感主义来到了,虽然是如此。
新闻业 - 我想认为 - 更像是客观传达新闻与您写作方式的艺术之间的交叉点,激发了阅读,移动的人可能会感觉到的人。实现产生可以获利的结果的具体目标并不是那么多。
同样,曲线的欧元偏差。听罗伯托(Roberto)谴责的话:具体,目标,产生,结果,可获利。这些是使曲线曲线的单词。他提供了什么话?艺术,灵感,动人,感觉。这些是您在寻求(主要是徒劳的)覆盖曲线时所依据的单词。
不久之后,其中一名美国人正在帮助将事情带回曲线。他对如何破坏新闻业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继续提炼内容收藏家,记者本身吗?``这可能会变成一个模型,而不是在《纽约时报》雇用数百个记者,而您可以让您有个人的自由职业者或个人博客作者拍照并写有关事物的文章,而A.I.汇总此信息以进行某种分布?
1958年巴尔的摩非裔美国人的记者
但这只能再次提高两色调的欧元感情主义。他不想生活在一个列表世界中。他认为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 - 想通过他们阅读的文章和他们所经历的艺术来提升,是的,当下,他们可能会屈服于点击诱饵,但他们希望超越即时性和本能。他大声想:A.I.帮助构建一个新网站,使您远离猫视频,远离BuzzFeed文章?
这也许是一座桥梁太远了。为抵消曲线而构建的工具?这种欧洲人性主义是如此极端,以至于现在造成了欧洲主义。罗伯托(Roberto),尽管按照房间的标准是非常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但不能接受。
是的,很抱歉,”他说。Facebook不是良心。您迷上了Facebook的事实 - 有原因。而且,是的,做一些使您远离聚会或所有其他事情的事情将是很棒的。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您最终要去了。很难改变某人的行为。
很难改变某人的行为:对于在A.I.工作的获奖者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想法。对于那些获奖者,就媒体而言,算法将不得不做更多的事情,而作家将不得不做更多的事情。裁员必须发生;公共话语的质量必须下降;媒体作为一个机构必须腐烂。作家将不得不成为永恒的筹款活动,取决于支持者的异想天开和观点。在斯坦福实验室中大量招募的技术公司将不得不控制更多社会信息。A.I.的建筑师知道,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可能会成为许多人的一个不愉快的未来,因为房间里的欧洲人类主义者的一部分似乎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您聪明,就像这些技术人员一样人们的生活和许多珍惜的机构遭受了痛苦。因此,如果您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就更加谨慎地提出了不可避免的事情,并且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变化无能为力。
在这里,在这个实验室中,人们看到了干扰的平淡无奇。在这里,您破坏了事情,因为您知道如何做的事情正在破坏事情。您对变量进行了优化,因为这些变量恰好是您知道如何优化的变量。您可以想像社会的整个片段,而没有提出人类的问题,因为压倒性的技术问题使他们拥挤了。您积累了别人会在坚持自己的阳ot中所经历的强大力量。您想到了用来破坏事物的工具,而不是问您需要哪些问题。And you did all this by convincing yourself that your own role was minimal, that you were merely riding atop the Curve.
***
The handful of Euro-humanists — now excluding Roberto, perhaps — wanted the room to own up to the real choices that they and the world faced. They wanted their colleagues to own up to the “moral character†of their work, to borrow a phrase from Phillip Rogaway, a cryptographer. Rogaway once wrote an essay criticizing his own colleagues for denying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ir work. “Cryptography rearranges power: it configures who can do what, from what,†he said. “This makes cryptography an inherently political tool, and it confers on the field an intrinsically moral dimension.â€
What he wrote of cryptography perhaps applied to A.I., too.人工智能。types could cast their field as “fun, deep, and politically neutral.†Their shallow optimism about the Curve undercut the need for bigger-picture questioning: “a normative need vanishes if, in 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 all paths lead to good (or, for that matter, to bad).†Technologists, Rogaway wrote, prefer to deny that their inventions can either benefit or harm the weak, depending on choices we make together.Technologists were, you could say, a bit like ostriches.
Roberto, having traveled to the Americanish side in the ongoing Euro-schism, was in full ostrich mode. “Facebook is not a conscience,†he had said. “It’s very hard to change the behavior of someone.†Then he brought up broccoli. It would be great if people wanted to buy pieces of broccoli at fast-food restaurants. But they don’t. So we have McDonald’s. The world is what it is. They were powerless to change it.
This gave Two-Tone Euro the opening he needed. People do want broccoli nowadays! And if such change was coming to food, why not to other things?
“Before McDonald’s, there used to be organic farmers,†Two-Tone said. “Then everyone wanted to step away from the old to McDonald’s, and now they’re going back. So in a similar fashion, people were like ‘O.K., let’s go for New York Times,’ now they’re going Buzzfeed, but they’re gonna come back.â€
Manoush, that champion of efficiency, had been following the back-and-forth and now tried to turn the conversation in a new direction.
“There’s a problem here that we’re not tackling, which is: how do you identify an atom of content, right?†he said. “So right now we’re dealing with articles’ being one atom of content. So I wonder if you can break that up further and further, and maybe you can figure out how much of that content to give to each person.â€
(One might note, as an aside, that even this style of diction aided the Curve view. Manoush, like many in the Valley, began a great many of his sentences with a declamatory “so†and ended a significant fraction with a faux-interrogative “right?†To speak this way was to leave no space for doubt, for choices that might resist forces, for the thwarting of inevitability. This way of speaking reinforced a view of the world’s problems as purely technical — the view that there was, in every situation, a right answer. “So…right?†was the opposite of “From where I sit,†or “but maybe that’s just me.†It rejected the idea that people have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needs and ideals. It rejected the very premise of politics. It dismissed the notion that there are competing values in tension in any situation, and that those values must be weighed and negotiated. It saw a world in which there was always a right answer, and technologists like Manoush had special access to those answers, and the rest of us should speak now or forever be quiet. So when I spoke, it made sense to cajole your agreement, right?)
***
So Manoush had been talking about how to identify an atom of content, right?
A neck stiffened just to Manoush’s right. Mahesh, an Indian techie n a white T-shirt, seemed perplexed by this idea of breaking up news into bits and algorithmically distributing the packages. “I don’t know,†he said, seeming a little lost. “It’s like, what is the goal here? What are you trying to optimize on?â€
Now this was a great question — perhaps even the question with which the session should have begun. What problem were they actually trying to solve?
But here was the problem with starting with problems. To start with the solution was easy: you looked at the tools you had invented and the Curves that were in progress and you imagined where the future would lead: If Uber wants to replace all the drivers by robots, do we want to replace all the writers by A.I.? To start with a problem was trickier, because not everyone agreed on what was problematic. Starting with a problem, your focus had to be on the society’s needs, not on your tools. Solving that kind of problem tended to involve democracy — collective action, contending values, the making of choices.
What was most striking about the meeting was what hadn’t been discussed.
No one had spoken of democracy and of the place of a press within it.
No one had dwelled on what happens to art in an era of free everything.
No one had reflected on the extraordinary market power of Amazon and the effect of that power on books and ideas.
No one had asked whether the society could protect itself against the Facebook News Feed’s tinkerers slipping their own biases into the algorithm.
No one asked these things, for to ask these things was to admit one’s own power and reveal to others their power, and to suggest that you and those others could decide what kind of future it would be, the forces and the Curves be damned.
Here these bearers of great power over the future seemed in denial of that power. The world would be what it would be.
Before the meeting ended, Two-Tone Euro got up, picked up what appeared to be a homemade hoverboard from the corner — a skateboard-sized platform with a cantaloupe-sized ball in its middle — and rolled away. Others mingled over the remaining pizza and drinks. Just outside, a man retrieving his bicycle from the rack was savoring what he had just imbibed upstairs. That room, he said, wonder filling his eyes, had collided some of the smartest minds in all of Stanford.
Some names and identifying details have been changed. All dialogue is quoted verbatim.